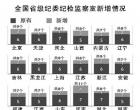核心提示
民俗驛站挖出真古跡
據(jù)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員介紹,按照原本總體規(guī)劃,此次發(fā)現(xiàn)的三處遺跡群所在地將建設(shè)成民俗驛站。但在建設(shè)之前,廣元市文物局委托四川省考古研究院,聯(lián)合廣元市博物館、昭化區(qū)文物管理所對(duì)昭化土基壩和擺宴壩進(jìn)行了考古調(diào)查和勘探工作,從而使這些深藏于地下的遺跡得以重見(jiàn)天日。
2014年7月至8月,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(lián)合廣元市博物館、昭化區(qū)文物管理所對(duì)廣元昭化土基壩和擺宴壩等地進(jìn)行考古調(diào)查和勘探工作,發(fā)現(xiàn)各類遺跡43處,其中包括疑似早期葭萌關(guān)的古關(guān)口遺址和四川首座被發(fā)現(xiàn)的西周時(shí)期城址等重大發(fā)現(xiàn)。考古專家稱,這座城址,無(wú)論是規(guī)模還是年代,堪稱為古蜀“第二城”,對(duì)研究巴蜀與中原地區(qū)交流和蜀道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。
考古現(xiàn)場(chǎng)負(fù)責(zé)人陳衛(wèi)東稱,目前,在三處遺址群中共發(fā)現(xiàn)遺跡43處,其中墓葬27處,建筑基址7處,古關(guān)口1處,城址1處,陶窯3處,灰坑4處。而此次考古最大的收獲就是發(fā)現(xiàn)了四川境內(nèi)第一座西周時(shí)期城址和春秋戰(zhàn)國(guó)時(shí)期的關(guān)口遺址,這對(duì)于古蜀國(guó)和蜀道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。
城址面積:
約5萬(wàn)平方米,類比7個(gè)標(biāo)準(zhǔn)足球場(chǎng)、小半個(gè)人民公園、大半個(gè)天府廣場(chǎng);或是當(dāng)時(shí)苴國(guó)首都
出土意義:
四川境內(nèi)發(fā)現(xiàn)的先秦時(shí)期第二座城(第一是三星堆古城),也是四川地區(qū)首次發(fā)現(xiàn)的西周城址
戰(zhàn)略要地:
地處巴、蜀、中原三方交界處和蜀道主干道上,巴蜀文化、中原文化等文化在此交融;巴、蜀及中原政權(quán)曾反復(fù)爭(zhēng)奪此地
來(lái)歷/
“或來(lái)自三星堆文明”
專家稱,此次考古,第一個(gè)驚人發(fā)現(xiàn)就是廣元昭化擺宴壩的古城遺址。從出土的陶片判斷,其年代應(yīng)為西周早期或商代晚期。目前已經(jīng)探明的城址面積約有5萬(wàn)平方米(相當(dāng)于現(xiàn)在7個(gè)標(biāo)準(zhǔn)足球場(chǎng);小半個(gè)人民公園;大半個(gè)天府廣場(chǎng)),規(guī)模僅次于三星堆古城,是四川境內(nèi)發(fā)現(xiàn)的先秦時(shí)期第二座城,也是四川地區(qū)首次發(fā)現(xiàn)的西周城址。
成都博物院副院長(zhǎng)江章華稱,根據(jù)在城址中發(fā)掘出土的陶片來(lái)看,其時(shí)代可能在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之間,文化與金沙遺址相同。雖然城址五萬(wàn)平米的面積在今天看來(lái)并不算大,但就商周時(shí)期而言,這種規(guī)模的城市已經(jīng)不能等閑視之,或許是當(dāng)?shù)卣?quán)的核心城市。
由于擺宴壩城址的存在時(shí)期也與三星堆王國(guó)覆滅時(shí)間相吻合,也有專家推測(cè),可能是三星堆人的一支北遷到昭化,并在擺宴壩建了新的城市。
地位/
“上海之于晚清”
據(jù)陳衛(wèi)東稱,由于苴國(guó)在建立后與新興崛起的巴國(guó)親善,并曾屢次與巴國(guó)聯(lián)手抗擊蜀國(guó)。因此他更傾向于苴國(guó)是從蜀國(guó)“分家”出來(lái)的獨(dú)立國(guó)家,而不是蜀國(guó)內(nèi)的封建諸侯國(guó)。故而,此次在擺宴壩發(fā)現(xiàn)的城市也有可能就是當(dāng)時(shí)苴國(guó)的首都。
據(jù)介紹,昭化地處巴、蜀、中原三方交界處和蜀道主干道———金牛道的關(guān)鍵點(diǎn)上,巴蜀文化、中原文化等多種文化隨著人員的往來(lái)在此交匯雜糅。上個(gè)世紀(jì)50年代,考古工作者在昭化寶輪寺地區(qū)發(fā)現(xiàn)了帶有明顯巴蜀文化色彩的船棺葬,今年五月又在昭化城壩發(fā)現(xiàn)了屬于中原文化的秦漢時(shí)期墓葬。僅就多種文化交流層面而言,其地位類似異國(guó)文化云集的上海之于晚清。除了文化上的交融之外,由于處在蜀道關(guān)鍵點(diǎn)上,戰(zhàn)略價(jià)值極高,巴、蜀及中原政權(quán)曾反復(fù)爭(zhēng)奪此地。因此,這座城到底屬于哪一國(guó),還有待后續(xù)考古工作印證。
兩道土墻 張飛夜戰(zhàn)馬超的“葭萌關(guān)”?
據(jù)陳衛(wèi)東介紹,此次考古發(fā)掘,另一個(gè)重大發(fā)現(xiàn)就是位于土基壩附近的上坪關(guān)口遺址。這處關(guān)口遺址平面呈長(zhǎng)方形,在探勘之后發(fā)現(xiàn)了東、西兩道夯土墻,其中西墻長(zhǎng)66米,東墻長(zhǎng)42米,兩道墻之間相距34米,夯土墻基礎(chǔ)厚約6-8米左右。從出土陶片判斷,應(yīng)屬于春秋戰(zhàn)國(guó)時(shí)期,而從兩道墻的分布和面積推測(cè),考古隊(duì)員認(rèn)為可能是早期的葭萌關(guān)。
據(jù)陳衛(wèi)東介紹,根據(jù)考古發(fā)掘來(lái)看,這兩道夯土墻的東面和南面底層下都是河沙。因此可以推定當(dāng)時(shí)關(guān)隘的南端就在兩河口的河道北岸上,而關(guān)墻的主要作用,除了用于防御,還具有防水功能。據(jù)陳衛(wèi)東推測(cè),關(guān)墻北側(cè)則延伸至跑馬梁一帶的小山包腳下,總長(zhǎng)度約有百余,當(dāng)時(shí)的蜀道主干道———金牛道應(yīng)該就是從這里穿過(guò)。
金牛道又名石牛道,相傳秦惠文王將一頭據(jù)說(shuō)能排泄出黃金的石牛送給了蜀王。蜀王派出五位力士,將這頭石牛從秦國(guó)拖回了蜀國(guó),他們所開辟的道路就是后來(lái)的金牛道。雖然傳說(shuō)虛無(wú)縹緲,但金牛道卻是真實(shí)存在的。這條道路自蜀中出發(fā),經(jīng)漢中,進(jìn)入關(guān)中,全長(zhǎng)約600多公里,地勢(shì)險(xiǎn)峻,是自古以來(lái)溝通中原和西南的重要道路,而此次發(fā)現(xiàn)的葭萌關(guān)墻不僅是蜀國(guó)北面的鎖鑰,也見(jiàn)證了蜀國(guó)的興衰。
據(jù)《華陽(yáng)國(guó)志·蜀志》記載,周慎王五年(公元前316年)秦大夫張儀、司馬錯(cuò)、都尉墨等率軍從石牛道伐蜀,蜀王自葭萌關(guān)出兵抗擊未果。戰(zhàn)敗的蜀王在武陽(yáng)被追兵殺死,而蜀國(guó)重臣和太子也在撤退至蓬鄉(xiāng)白麓山后被殺,蜀國(guó)就此滅亡。
陳衛(wèi)東說(shuō),目前考古工作重點(diǎn)之一,就是在關(guān)墻附近尋找當(dāng)時(shí)的道路遺跡。據(jù)三星堆工作站站長(zhǎng)雷雨稱,蜀國(guó)被秦滅之后,一部分蜀人貴族被秦人遷徙到了關(guān)中的寶雞等地,之前的考古發(fā)掘在這些背井離鄉(xiāng)的蜀人墓中找到了蜀地風(fēng)格的隨葬品,而這些貴族的遷徙路線一直是未解之謎,而此次在昭化發(fā)現(xiàn)的遺址群可能會(huì)為解開這個(gè)謎團(tuán)提供幫助。
成都商報(bào)記者 徐劍簫
援引:《三國(guó)演義》(第六十五回)中最經(jīng)典、最男人的一場(chǎng)單挑表演賽就是在葭萌關(guān)舉行的:張飛挑燈夜戰(zhàn)馬超。傳說(shuō)劉備圍攻成都,劉璋求救于漢中張魯,許割二十州之地。馬超自告奮勇率軍攻葭萌關(guān),守關(guān)霍峻、孟達(dá)不敵,劉備自率張飛馳救。二人對(duì)敵,一番惡戰(zhàn);張飛與馬超大戰(zhàn)二百余個(gè)回合,不分勝負(fù)。天色已晚,點(diǎn)起火把,換馬再戰(zhàn)。劉備見(jiàn)馬超英勇,心中甚愛(ài),叫二將休戰(zhàn),派李恢說(shuō)降馬超。馬超雖有猶豫,但衷心贊佩劉備,遂成歸順之事。今日葭萌關(guān)關(guān)前的石階小道,多數(shù)石階已很光滑,傳說(shuō)是張飛大戰(zhàn)馬超的戰(zhàn)場(chǎng)。
(原標(biāo)題:第二個(gè)三星堆?)